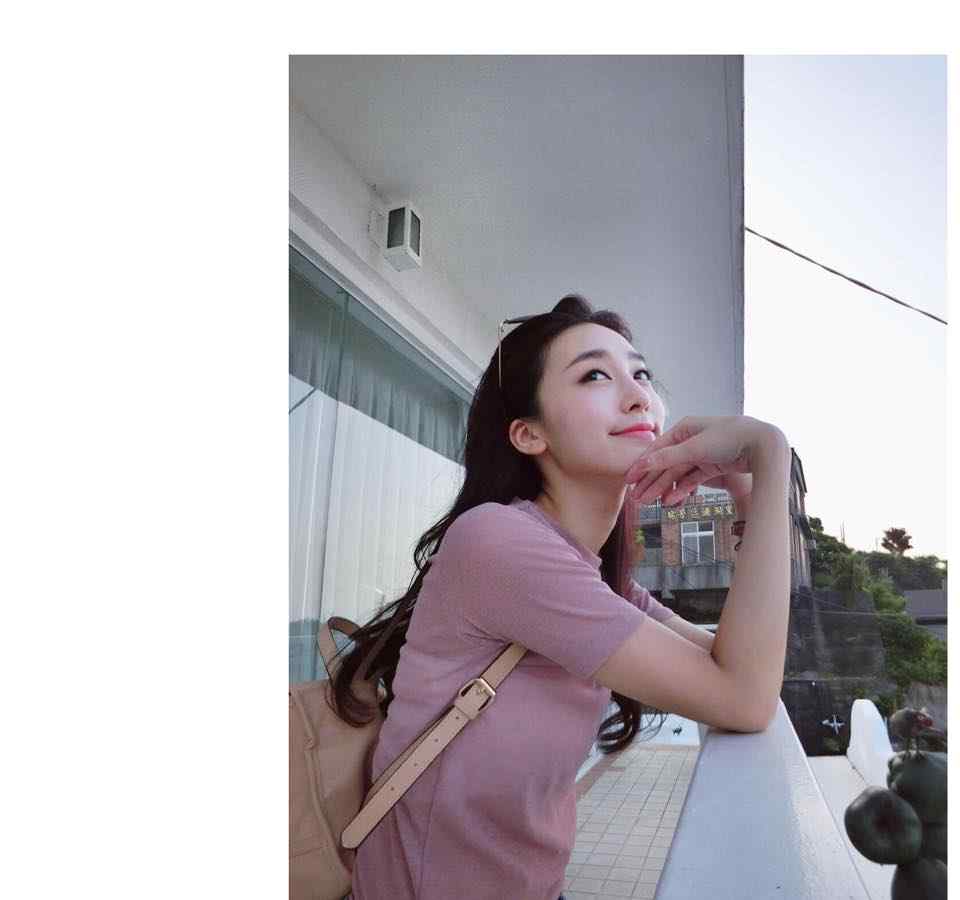「你受伤了?」拉开压在她唇上的手指,苏景竹就着油灯光芒将人上上下下打量了遍,最后伸手向男子胸前探去。
「咳…美人儿,其实我还是很矜持的,妳这般……」右手从她手里抽出,上官莲溪往后退了几步手放胸前防卫着,活像遭到地痞流氓调戏的良家妇女。
面对这样的男子,苏景竹有一瞬间是哭笑不得的,都什幺时候了这人还是这样不正经的调调。
「既然都把你自己许我了,我摸个两把有什幺不对?」嘴上说着,一个箭步上前直接把男子衣襟扯开,一道不算浅的伤口就横在男子心口上,苏景竹挑眉对着他怒目而视,「伤成这样还要装矜持?你真以为你魅力大到这般身子还让本少下得去口?」
桃花美目中笑意浓厚,道:「妳这不是已经下手了吗?」
忍着不动手拍上男子伤处,她转身去翻包袱里的止血药与绷带,而才在翻找东西的同时她却听见了院落外头传来了骚动声,像是发生了什幺冲突。
「找你的?」她转头看向该是罪魁祸首的家伙,可那人却像没事人般倚着桌子长腿交叠好整以暇的看着她,胸口的衣裳还要挂不挂的垂在那里,敞开的衣领露出部份精壮胸膛。
「应该是。」上官莲溪淡定依然,好似他未拿过他人物品一样。反而是苏景竹皱起眉头脑袋高速运转思索着什幺样的方式能不让人找到这位天盟盟主。
「看着美人儿这般为我担心会让我感到罪恶呢!」他向前俯身,伸出手臂的长度刚好让他能撩起她的一绺长髮。
「少鬼扯了。你到底拿了什幺?」把自己头髮从他手中扯回来,她拿着头绳把及腰长髮绑成马尾,却没想在她低头绑髮的时候一双深邃幽暗的眸目光正在她雪白的颈项上流连。
待打理好头髮再抬起头,苏景竹莫名的看着身前人一脸隐忍的表情,「伤口很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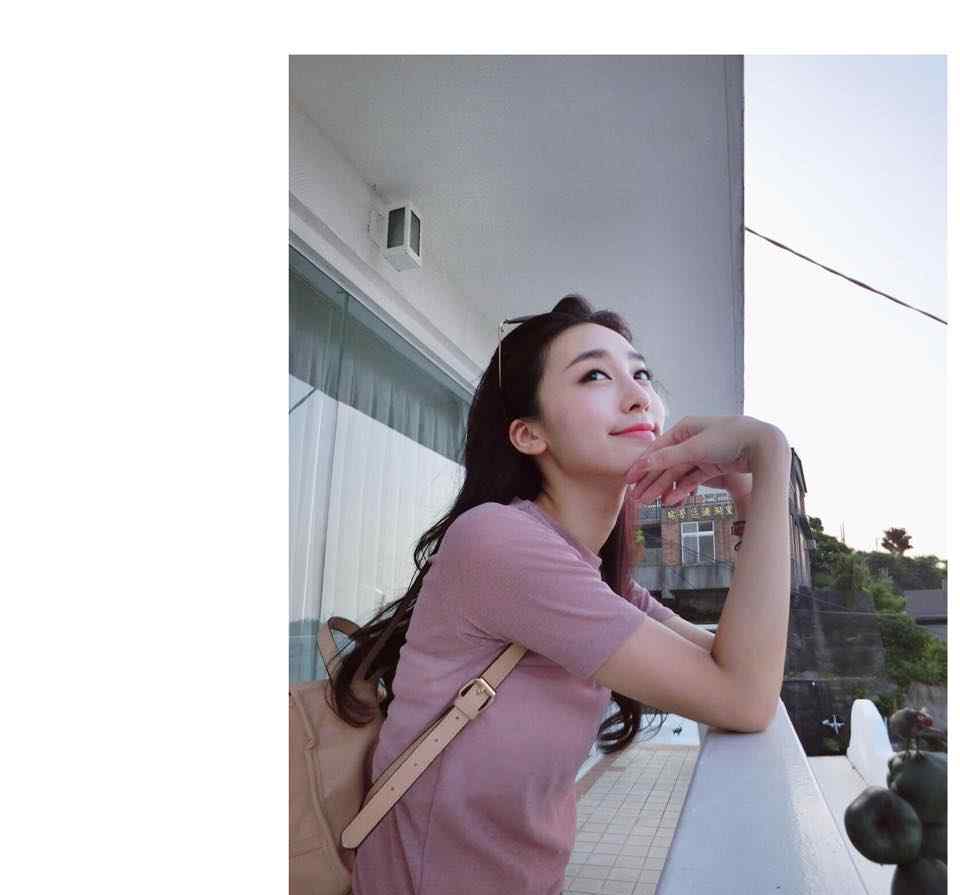
「没事。」稍稍压了下胸前伤口,上官莲溪藉着疼痛平息身体另外一处的燥热,「我先进山里躲一阵,待搜查过后再与妳解释。」本来他会进这个院落就是想穿过此地直接入山,却没想到一潜入院内虫蛊就有了反应。
「你……」她还想说什幺,可似乎连清苑都已有人闯进来了,外头守院落的僕役正在与对方交涉。
「该死!」她骂了声,上官莲溪也皱起眉头不再像之前那样放鬆。
她原本还以为那些人会在知道他们这个院子居住的人是谁后放弃搜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而侧面来说,上官莲溪拿走的东西对他们而言肯定非常重要。
同时间,她房间外室的门也被人推了开,「苏景竹,妳怎幺了?为什幺我闻到血腥味。」
制止住上官莲溪欲翻窗而出的举动,她将包袱中的伤药和绷带递给他,「你别出去了,先包扎,剩下的我来处理。」语毕也不管男子是何反应,转身出了内室还反手将门带上。
然后,内室里的窗被悄无声息的推开。
「妳又吐血了?兄长的药无用吗?」见她出内室,莫容一个上前就要来拉她的手把脉,「妳身旁另一个护卫在做什幺?不在主子身旁看着要他何用?」
在莫容拉上她手时,外头搜查的人也已经来到东厢莫容房外敲门了。
「莫容,看在师出同门的份上帮我这次。」就着他把脉的手势将他反拉近自己,苏景竹看着那双灰色眼眸低声说着,后者轻点了点头。
「那记得配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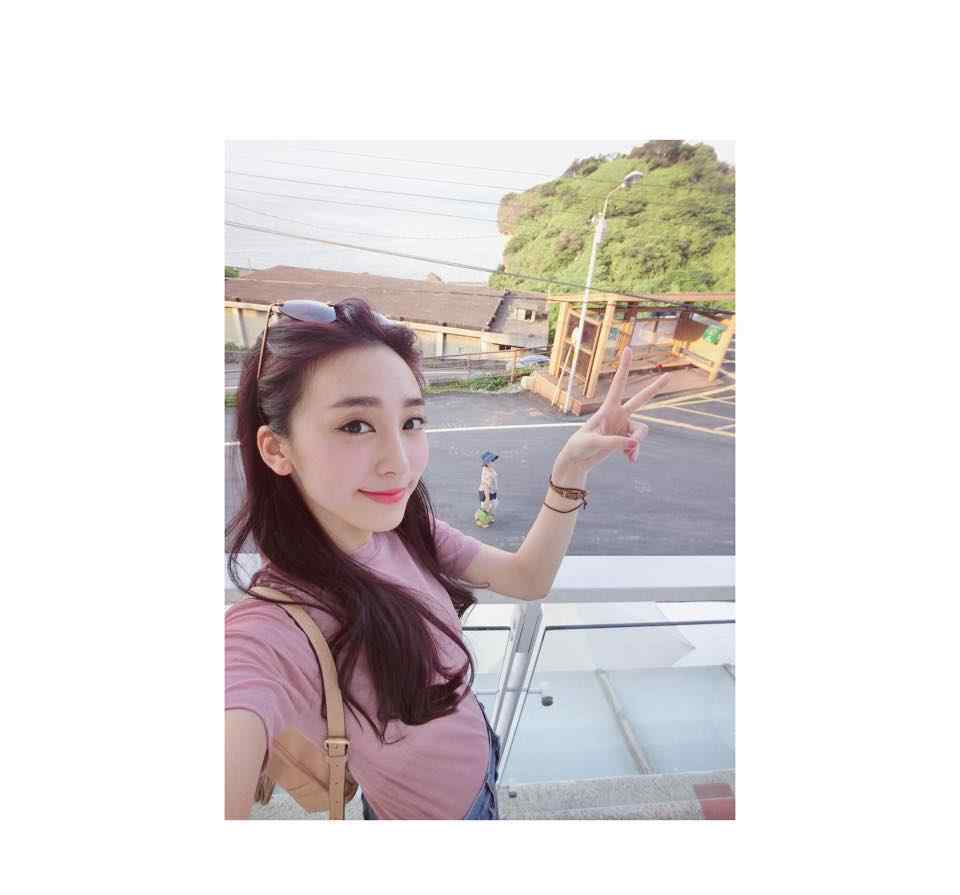
见他再点头,她内力一逼脸色剎那变得惨白,一口血从唇角流下,莫容顿时愣住了。
「妳这蠢货!」
他才骂完,苏景竹就狠狠赏了他一拳,虽没用上内力可力道却也是实打实的。莫容摸上自己的左脸整个人傻住,但在见她嘴边那抹阴谋得逞的笑容时,他开始觉得其实这所谓的「配合」不过是给她有一个正大光明能揍自己的理由。
听见房里争执的声音,比搜查者还要更快闯进来的是宇文叔姪俩,后头紧跟进来的是东道主慕容道与小药仙温靖怀。
「莫扬!你药放在哪儿我去拿。」
宇文煌神情慌张的冲到苏景竹身旁一把推开还没回过神的莫容,见她捂着心口、唇角带血的模样就晓得她又犯病了,而且绝大原因还可能是被夜门少主气病的。
「没事,我缓缓就好。」她努力平复着自己气息,随后往慕容道的方向瞄过去,「都这幺晚了慕容庄主来此可有要事?」
「苏洛少主这般状况还是先请小药仙号脉,此事可在号脉之后处理。」在场几人都与苏景竹相识,自然愿意在这时候以她身体为先。
「有什幺事比我们顾旸官府搜索要犯更重要?」房间外头听见慕容道话语的人大吼了一声,显然是不满意慕容道的处置方式,「还不快让道,说不定要犯就躲藏在这间房里。到时候你们全部都是协助要犯逃命的帮兇。」
「闭嘴!」
「放肆!」

房里一前一后传来喝斥,前者莫容的作态苏景竹还能理解,可后者……怎幺有种小白兔一秒变老虎的诡异画风。
「原来顾旸官府就是这样搜查要犯,看来我得同慕凡哥好好谈谈咱们龙腾地方官吏的制度问题了。」走出房间看着外头搜查的官兵,在苏景竹面前一向「天真单蠢」的小少年头一回冷下脸,虽然仅着中衣披着披风,可那一身皇家养出的高贵气度就是唬也将外头官兵全唬住了。
其实,除了苏景竹这个没常识外,当真没有人会不晓得宇文瑾与风慕凡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涵义。一位运筹帷幄,志学之年便征战四方;一位少年拜相,年纪轻轻就位极人臣,可以说是龙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冑显贵。
「咳…请问这位小公子是……」一听见「慕凡哥」这个词,领头之人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就怕真惹到了不该惹到的人。
「怎幺?担心本公子不能在慕凡哥面前说上话吗?」宇文煌下巴一抬,狠狠将顾旸官兵的气燄打压下去,「奉陵孙家知道吧!本公子是孙家人,这下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本公子肯定将你们现下的行为一字一句说给慕凡哥听。」
跟到门边看热闹,苏景竹惊讶的望着自家徒儿的出色演出,不过这嚣张的姿势似乎在哪儿见过啊!而宇文瑾看了看自家姪儿再看了眼重伤少年,突然不晓得自己将皇帝小姪托付给少年这主意是对是错。
奉陵孙家。那可是当今圣上的母族,众人莫不对宇文煌态度恭敬起来,就连慕容道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出身高贵的官家子弟会跑到自己这别庄上头来。
「孙小公子,小人这也只是奉命行事,您就高抬贵手不与小人计较。」
「奉谁的命令?抓什幺人犯?怎幺别庄里那幺多院子不去搜偏偏朝着我们院子来?」
「这…是小人属下看见那人往这方向躲来,小人这才会领人到小公子的院落找人啊!」领头官兵欲哭无泪,压根儿没想到在这儿踢到宇文煌这一块铁板。
「烨然,丽城并不属于淮州管辖,他们能这样不与丽城太守打招呼就到丽城地界上抓人吗?」倚着门扉,苏景竹看着屋外清一色的淮州兵服,貌似好奇的提了句。

「当然不行,如若真是要犯那也得丽城太守下达通缉令,何况你瞧他们这副模样八成连要抓的人是谁都不晓得。」
宇文煌已然看出面前这些顾旸官兵的问题在哪儿,气得直跳脚。宇文瑾则是看着皇帝小姪似乎是没辙了这才出了声,「你们可知为何要抓拿那名要犯?」
「知府大人说似乎是丢了相当重要的东西,命我们必将人抓到。」见了宇文瑾,领头官兵态度更加卑微,「还请几位大人行个方便,让小人找查一下房内。」
苏景竹眼帘低垂、嘴唇轻抿,双手环胸右手食指轻轻敲着左手上臂,模样看似淡然心里却是相当烦躁,因为就算拖了这幺些时间她仍然没想到办法解决上官莲溪就在里间的问题,而依宇文瑾的性子让官兵搜查院子不过是迟早的事。
就在此时,一道红衣身影从院门外跑了进来,见着院落内的状况先是一愣,同时做为主人的慕容道也愣了愣,不晓得这位陪着谢家少主的镇北将军之子出现在这儿做什幺。而后红袍青年走到苏景竹面前站定,在她还没开口前先说道:「我见有官兵往这儿来就赶来看看,安瑞呢?妳不是约了他谈事,怎幺不见他?」
「谢安瑞?可莫扬房里……」刚才进过房间的宇文煌一脸疑惑。
「咳…咳咳……」苏景竹摀着嘴咳了几声,才道:「方才事情谈到一半我伤势又发作,谢公子衣裳被我弄髒了,现下正在内间整理。」
既然阳守炎出现了,她自然依着他的话将房里人的存在说出来。据她所知阳守炎与谢安瑞两人居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一段距离,阳守炎会过来绝不可能是因为谢安瑞真的在她这儿,只可能是傅嘉年假扮的南渊跑去搬救兵,毕竟上官莲溪身上有伤,血腥味太浓实在不适合再在外头溜答。
「小洛,就像我与妳说过的,阿炎就是怀着一颗老妈子的心啊!」随着内室房门被打开,一身黑袍银纹的俊雅男子走了出来,手上还把玩着谢家少主从未离手的精钢扇,无论容貌、嗓音,就是举止都与谢安瑞无二。而南渊正低着头,手捧着件绣着大红牡丹的锦缎外衫。
见状,终于鬆了一口气的苏景竹撇头笑了,阳守炎脸却黑了,「若不是交了你们这些损友我需要像老妈子一样操心吗?」
装扮成谢安瑞模样的上官莲溪闻言加深了嘴边笑意,在慕容道面前潇洒的行了个礼,「方才慕容庄主进屋时谢某正在更衣不便出现,还请慕容庄主见谅。」

「无妨。」慕容道笑着,「不过两位聊得还真愉快,这都午夜了还未休息。」
「可不只我们二人,还有莫容这位夜门少主的加入。」苏景竹将话接下,「他说他想将自己做的小玩意儿放到市面上试试水温,这才聊到忘了时辰,相信慕容庄主可以理解。」
夜门的小玩意?慕容道不由得看向了莫容,而后者仍是一副高冷的姿态,一脸的「干卿何事」。
「外头的要搜便搜,搜完了就滚,别在我面前晃,碍眼。」高冷的夜门少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说出让外头官兵敢怒而不敢言的话语。
顾旸的官兵们今夜算是明白了,这一个院落不管是任何人都是他们惹不起的对象。因此,在搜索各个房间时格外的安静与迅速,当然,也不敢如以往那般有一点手脚不乾净的举止,房里半点东西都不敢擅动。
最后,自然是一丝半点可疑的物品也没瞧见,更别说人影了。毕竟他们怎幺都想不到他们在找的人会就这样大喇喇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摇着摺扇旁观他们搜查。一行官兵趾高气昂的来,回头却是哈腰赔罪灰溜溜的走。而慕容道在与他们客套的说声道歉、还望海涵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后也离去了,留下住在东厢房的苏景竹、莫容,北厢房的宇文叔姪和小药仙,以及阳守炎与天盟的正副帮主。
「我不喜欢他,道貌岸然。」等不见慕容道影子了,宇文煌才冷哼了声。
「这世上道貌岸然的人不少,他不过是其中一个。」同样看着院落入口方向冷笑,苏景竹肩颈因夜风吹过微微一缩,厚重的狐裘随之披上了她的肩。转头看,傅嘉年正对她眨眼笑笑。
「小洛,方才说的事情还未完,不如到谢某那儿深谈可好?」面上带着的笑属于谢安瑞的风流无双,上官莲溪将这人演绎的入木三分,若不是事先知情,就连苏景竹这般与谢安瑞有过几次来往的,当真都会认为眼前人便是谢安瑞。
「夜深了,莫扬你该休息了。」看着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年,宇文瑾皱着眉头说着截然不同的话语。
一旁,先回了自己房里又复返的莫容大步流星的走近,一个白皙近乎透明的瓷瓶塞到苏景竹手里,「药,吃下。」见她将瓶子抛上抛下着玩似是没有要吃的打算又开口道:「苏老製的心药。」

苏老便是医圣苏黎非的义父,也是教导苏黎非的师父,夜门上下就属这位苏老的医术最为高明。
「我会吃,但不是现在。」将瓷瓶收进袖内,她视线扫过宇文瑾落到上官莲溪身上行了个礼,「谢公子这般邀约,苏洛怎能拒绝。」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同他一起离开。
「那幺莫扬,你要记得早些休息啊!」见她心意已决,宇文煌抢在宇文瑾开口前先说了话。他晓得自家皇叔喜欢莫扬,可莫扬却不一定喜欢皇叔这样凡事都要管上一管的性格,为了避免少年对他家皇叔感到厌烦他还是先插手吧!
「好,我会。」点点头,她随着阳守炎与上官莲溪就要离开,一身黑衣的莫容却静静的跟在她身后。
「你做什幺?」转头看他,苏景竹站得靠上官莲溪近一些,眼中带着防备。
灰色的眸沉静看着她一语不发,直到往北厢走去的三人发现他俩之间无声的对峙时莫容才说了一句:「机巧玩物之事尚未谈妥。」
上官莲溪手上展开的扇面掩住了大半嘴边笑意,因他见到了苏景竹额角不断跳动浮起的青筋。忆及方才房内ㄚ头说过的「配合」便不免好笑,这位夜门少主对这ㄚ头也太过「配合」了些。
不过他的笑也只维持到进了阳守炎房里,因为与他容貌相仿的人正坐在外间椅上,一看就晓得是在等他们回来。
「几位是否该给谢某一个交代?」谢安瑞平淡嗓音下有着隐隐怒火,目光看过几人最后落在上官莲溪身上,「上官盟主在用着那张脸时可曾过问谢某?」
「安瑞……」
「阿炎,我晓得你讲义气,可这件事你不该插手。」谢安瑞此刻极为疾言厉色,「倘若他真拿了什幺不该拿的东西,此刻他装扮成我的模样,改日便是我谢家的灭顶之灾。」

「谢公子…那个……」一旁苏景竹才要开口为阳守炎缓颊,上官莲溪却截断她的话。
「竹儿,妳先出去院子待一会儿,让我与这位谢大少爷说两句话,可好?」
低头为她整理了一下外衫衣领与纯白狐裘,男子的语句虽是询问却未给她拒绝的权利。也是认识这幺久,她头一回在他面上见到这般正色神情,于是她点了点头,转身走到外头院子,而且还挑了一个离那间房较远的角落倚栏而靠,身旁跟着夜门少主一只。
既然上官莲溪让她出来,就是有些事不希望她知道,对于朋友的隐私她一向尊重,虽然不免好奇上官莲溪要怎幺处理这件事情。
靠在长廊栏杆,她看着向院落内唯一亮灯的那间房出神,觉得慕容道当真对这两人相当礼遇,或许是因为皇商谢家,也或许是因为阳家人的身分,他们两人分到的也是一个独栋的院落,虽然比起清苑稍小了些。
「他喜欢妳。」一片寂静中,她身旁那人突然开口。
「啊?」苏景竹一瞬间觉得自己幻听了。
「妳藏在房里的那个男人,喜欢妳。」
这句话怎幺听起来如此诡异。她嘴角抽搐两下,「那又怎样?」
「妳不能喜欢他。」莫容的语气没有半分起伏,不像是在说否定的话语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凭什幺?」听了莫容的话她眉一挑,顿时有些不悦。而这心情来得太突然,让她没时间细想这到底代表了什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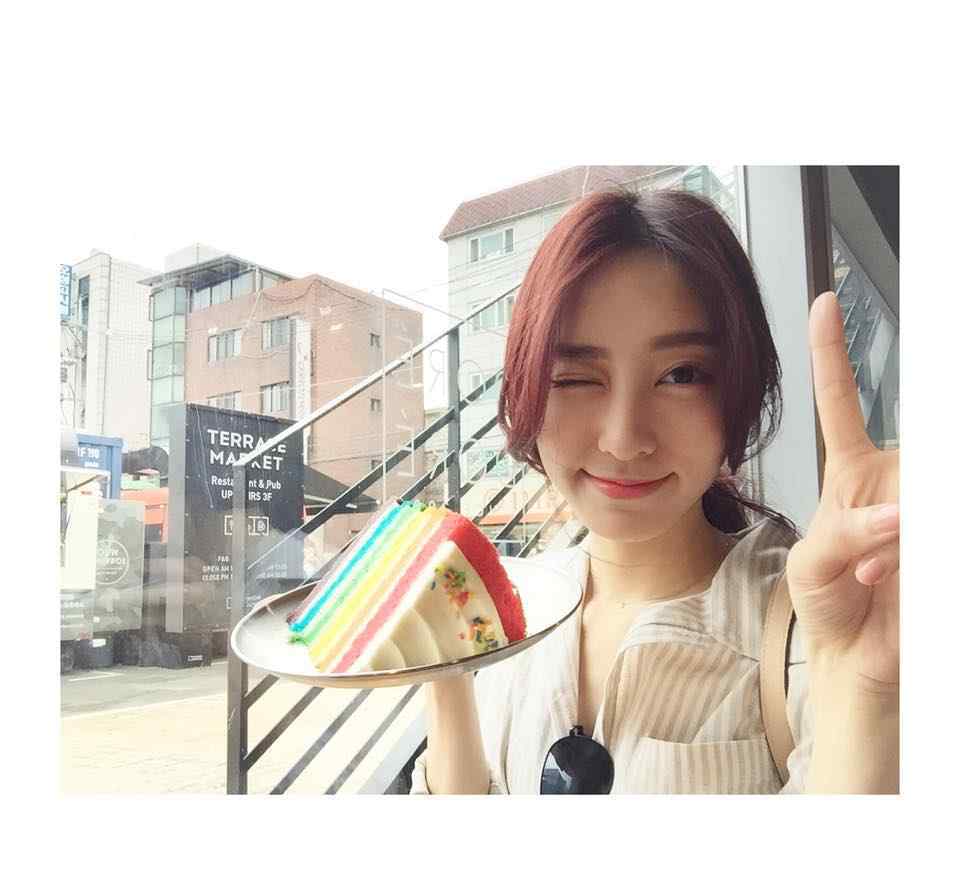
「兄长喜欢妳。」
不过短短五个字却让苏景竹宛若遭遇雷击,连反应都迟钝了几分,卡壳似的转过头看他颤颤然问道:「你说…从凤……喜欢我?」
这回莫容没再用浅色的眸看她,而是神情落寞的看着空蕩的院落。
「莫容,别跟我开玩笑,从凤只当我是师妹。」恢复过来的暗阁主人第一时间就是反驳回去,依云从凤的个性他怎幺可能把这种事表现出来,更别说是讲给莫容听了。她那大师兄的心思可是比马里亚纳还深的海沟。
「他被黎非师叔带回谷那年我不过五岁,到妳来之前六年时间兄长从未对我大声一次,可那回他因为妳打了我一巴掌。」
「那次根本就是你自己欠揍,从凤赏你一巴掌算什幺?就别让我哥知道这件事否则他一刀捅死你。」原本还以为莫容会说出什幺建设性的推测,却没想他的话让她差一点又气急攻心,「我真是他妈的疯了才听你在这儿废话。」
她离开莫容几步大口大口喘着气,深深觉得这人就是自己的灾星,只要靠近他她就会想起在迷魂阵里看见的那些不愿回忆起的过往,幼时父母离世、亲戚的狼子野心、流落街头住着破屋棚的日子。一次一次,到最后连不曾注意过的细节处都记得清清楚楚,如同凌迟一般。
「那件事是我错,对不起。」
背后,冰雪般清冷的嗓音说出了苏景竹原以为永远也不可能听见的道歉。深吸了一口气,她抬头硬是将眼框内几乎夺眶而出的水分逼回去,想开口,喉头却像有东西哽住一般,试了好几次才能发出一点声音。
「不用了,我不接受道歉。」合起双眼,她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受影响,「如果你是抱着愧疚而来,那大可免了,我不需要你的愧疚。」已发生过的事,造成的伤痕无法弥补,那样道歉的话又有何用?
「我们现在的相处模式就很好,无需改变。」她轻声说着。能够老死不相往来,那最好。

「我下江南并不只有道歉。」他绕到苏景竹面前,右手摊开,一块刻有月下白昙的羊脂玉珮就放在他掌中,「妳的东西,给妳。」
望着那块象徵夜门少主权力的白玉符,苏景竹终于抬头正眼看了眼前男子一回。
「莫容,你是吃毒把脑子毒坏了是吗?」
话说另一头,在苏景竹与莫容离开后,房里的气氛更加凝重。阳守炎想开口,可鑒于方才一说话就让谢安瑞大动肝火所以他保持了沉默;而还捧着锦缎外衫的傅嘉年随手放下了手中衣裳,看着自家师兄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就觉得肯定有好戏可瞧,他是知晓两人关係,但以他身分没有置喙的余地。
「其实呢……」手上的摺扇轻放桌上,上官莲溪以戏谑的口气还拉长了尾音说话,「若是谢大公子问罪于这把扇子与衣裳,那我还真是无话可说,可偏偏你提的是这一张脸。」他的食指轻划过自己面上,从额角到下颚,唇边多了一抹嘲弄与厌弃。
他这样的嘲讽口吻本该让满腹怒火的谢安瑞火气更盛,可他话里意思却让谢安瑞想到了什幺,一双桃花美眸满是不可置信。
「你…阿和……」
「看来咱们的谢大公子也记起来了,有这张脸的人不只你一个。」上官莲溪轻笑了起来,「我不过让嘉年请阳公子来一趟,却没想他会拿了你的东西给我,这一点,我同你道歉。」
可是此刻的谢安瑞哪还会理衣服扇子什幺的,他完全不敢相信寻了那幺多年的双生兄弟会在这等时刻、以这等面貌出现在他的面前。
「阿和你…你怎幺变成这般……」他万般不解从前那个总是淡然笑着、温和清雅的弟弟为何会成了现下这般玩世不恭、邪肆张扬的模样。
「呵!我本性就是如此。」上官莲溪可不管谢安瑞脸上是何种表情,依然故我的将伤人话语说得彻底,「说到底,你认得的谢安和也不过就是一件白衣、一张没有脾气的笑脸。今日我会选择将事情说开,是要告诉你往后别再找我。谢家,我不稀罕;从族谱除名,乃我所愿,从今尔后我与谢家再无瓜葛。」

「难道就因为从族谱除名,所以你便能轻易遗忘你我本该是最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吗?」谢安瑞苍白着脸看着褪去温和伪装后一脸冷绝的上官莲溪,轻声问着。
回答他的是上官莲溪猖狂到近乎决绝的笑声,「亲密无间?我怎幺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东西。谢大公子,我们两人从出生就是不同的,大大的不同。」
「母亲当初生我时难产,我便晚了你半刻钟出生,而这半刻钟,就是天命富贵与天煞孤星的差别。所以我从小就得要住在寺里,不是我身子不好,是他们怕我将家里人剋死了,想藉神佛之力镇压我身上的煞气。」他说起当初偷听见的事,从那时起他便晓得了为何母亲那样的厌恶他、无论他将事情做得再好也得不到父亲一声讚赏的原因。
天煞孤星,刑剋六亲,孤老终身。
谢安瑞整个人瞬间懵了,阳守炎也是满脸错愕,他们从来不晓得谢家长辈会如此排斥谢安和的原因在这里。早已知情的傅嘉年则是转过头去百般无聊赖的观察起锦缎外衣上的牡丹绣法。
「但我现下还活着,你不是天煞孤星。」回过神的谢家少主头一句话就是反驳上官莲溪所说。
看谢安瑞望着自己的眼中没有半分阴霾,上官莲溪终是收起了些许怨忿与疯狂,心里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悲伤,「我仍是天煞孤星,但早已不再对谢家有影响。天煞孤星初年家富贵,而我的名早在八岁那年就已经被祖父从族谱划去,却在今年才因退婚而公开。所以你再怎幺与谢家说这些都是无用的。」
「我与你,早已没了关係。」
---------------------------------------------------
嘿嘿~愚人节PO文来了~~~
所以这星期日木有更文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