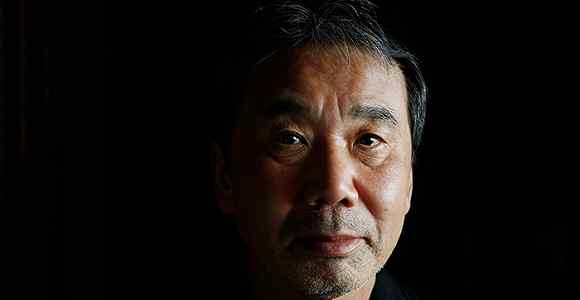村上的著作似乎在说,生活也许一直很奇怪,但是梦魇终会结束。你会找到丢失的猫。

我们在曼哈顿会面的前一天,一个女人在中央公园拦住了正在晨跑的村上春树。“打扰一下,”她说,“您不会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小说家吧?”一个略显奇怪的提问方式,但是村上还是用他通常的平静语调做了回答。“我说,‘不,其实我只是个作家。但是,仍然很高兴见到你。’接着我们握了握手。当人们这样拦住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不过是个普通人。我实在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想见到我。”
把这番话理解成虚伪的谦虚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把它理解成真的对名望感到不适同样不正确:只要有机会,69岁的村上总是会说,对于他的全球声誉,他既不期盼也不排斥。与之相反,他的观点是,他是一个充满好奇而略显困惑的旁观者——观察着从他的潜意识里冒出来的超现实故事,也观察着这些用日语写成、又被翻译的故事吸引了数百万读者的现实。村上的典型主人公都是相似的超然观察者:安静、社交上很孤僻、籍籍无名的30多岁的中年男人,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会激起他的好奇而不是恐慌,或者找寻丢失的猫,结果却闯进了梦幻般的平行宇宙,里面充满了爆炸的狗、穿山羊服的人、神秘的青春期少女和没有面孔的人。
苏联解体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然后我的书就变得非常流行了。
村上的理论是,尤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这种吸引人的文学配方特别奏效。“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我特别受欢迎,那时苏联刚刚解体——社会十分混乱,困惑的人们就会喜欢我的书。”在美国代理商办公室的一间会议室里,他一边喝着水,一边解释道,“在德国,当柏林墙倒塌,混乱也接踵而至——人们也就开始喜欢我的书。”如果这套理论正确,那么他的第14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之下的美国和脱欧的英国会特别有市场,这是一部长达674页的小说,里面充满了村上的奇异特色,由菲利普·加布里埃尔和特德·古森翻译,10月9日在英国出版。
村上把新作的情节总结为“抢劫的游戏”:书中无名的叙事者是一个最近刚被妻子抛弃的、忧郁的人像画家,他想要摆脱旧生活,于是前往日本东部的山区,踏上了一场复杂的冒险,期间遭遇了神秘的科技企业家,在夜里自发响起的铃铛,井中的地下神龛和其他地下教堂,还碰到了村上标志性的遗失的猫,以及一位两英尺高、特别健谈的武士,他是从叙述者在阁楼上找到的画布里走出来的。

在政治焦虑的年代,村上的作品就会变得流行,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入口,有时候几乎成了读者的镇定剂,情节发展的奇异被情感上的平淡所抑制,读者会感到从现实世界的极端状态逃了出来,在他的作品中获得了安慰。村上曾告诉记者,他喜欢棒球是“因为它很无聊”,在2007年的回忆录《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什么》中,他赞美了跑步的愉悦,因为跑步时他可以摆脱任何感受,暂时得到休息。
然而,你不能指望村上告诉你,作品中那些幻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创作都是基于潜意识:他认为,如果一幅画面从黑暗幽深的内心里冒出来,那么它必定是有意义的——他的工作只是去记下冒出的内容,而不是去分析它。那是“聪明人”的工作,他说着,脸上皱缩着笑容,“作家不必表现得很聪明。”比如,2002年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个场景是鱼像冰雹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人们问我,‘为什么是鱼?而且为什么它们要从天上落下来?’但是我没有答案可以给他们。我只是得到一个想法,某些东西应该从天上落下来。然后我思考着:什么东西该从天上落下来呢?然后我对自己说:‘鱼啊!鱼会很不错。’”
“你知道,如果那是我冒出来的想法,或许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某些来自潜意识深处的想法会让读者产生共鸣。所以现在读者和我有了一个秘密的会面地点,它在现实之下,是潜意识中的一处秘密场所。在那里,鱼从天上落下来完全正确。在这处会面地点,分析象征或与之类似的其他事情都是不相干的。我把这些事留给智者。”村上将自己视作一个管道——连接着他和读者的潜意识——这相当明显,在谈到他是一个“自然的故事讲述人”时,他甚至停下来纠正说,“不,我不是故事讲述人。我是一个故事观察者。”他与这些故事的关系就像梦和做梦的人,这大约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说自己晚上几乎从不做梦。“是的,也许我一个月就做一次梦,”他说,“但是我通常不做梦。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常常在醒着的时候做梦,所以当我睡着了就不必再做梦了。”
村上成为作家的关键时刻,正是这种感受从某个地方冒出来,这种感受不受意识控制。村上1949年生于京都,那是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的时期。因为放弃了公司的工作而改行在东京开爵士乐俱乐部,他的父母对他很失望。他的俱乐部叫“彼得猫”,以他的宠物命名。几年后,他在棒球馆的站台上看着美国球手戴夫·希尔顿将球打飞出去,这时他突然冒出了写小说的想法,此次顿悟带来了《且听风吟》。不久后的一个周末,一通来自日本文学杂志《群像》的电话将他吵醒,通知他这部小说入围了新人奖,他挂断电话,然后与妻子阳子一起去散步。他们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鸽子,并把它送到了当地警察派出所。“那个周日明亮而清澈,树木、建筑、商店的橱窗都反射着春光,美丽可爱。”几年后,他写道,“那时这个想法击中了我。我将赢得这个奖项。我要变成一位小说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是那一刻我很确信事情会这样。完全确定。不是用推理的方式,而是直接地、直觉地肯定。”
60年代,我们相信如果努力世界就能变得更好。现在人们不信这个了,这让人有点悲哀。
在日本,批评的声音渐渐涌上来。“在日本文学界,我是害群之马。”村上回忆说——部分原因是他的书缺少任何根源于日本的意识,里面充满了美国文化元素,被评价为“太像美国小说了”。“我们在战后出生,都是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我听着爵士乐和美国流行歌、看着美国电视剧——这些是朝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但是无论如何,不久后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既非美式,也非日式——我的风格。”
无论如何,无论批评家怎么想,他的商业成功稳步增加,1987年的《挪威的森林》达到了一个高点。这是一个对青年恋爱的怀旧故事,一年内就售出了350万册。这本书是以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的,这是村上再也不会在小说里采用的风格——尽管按他自己来说,如果认为那些降落的鱼和带着超自然气质的女性的故事不是现实主义,他必定会反对这种说法。“这是我的现实主义,”他说,“我非常喜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认为他的写作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是我不这样认为。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我的风格就像我的眼镜:透过这些镜片,世界于我而言才有意义。”

随着地位提升,他的日常写作程序也开始变得熟练,现在他变得和他的每一部小说一样出名:每天四点起床,在进行至少6英里的跑步或者游泳之前,写作5到6小时,一天能写出10页。“掌管爵士俱乐部时,我的生活特别失序和混乱——老是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上床睡觉——所以当我变成一名作家,我决定过一种非常稳定的生活:早起早睡,每日锻炼,”村上说,“我的信念是,为了写坚强的东西,我要在身体上变得强壮。”他也许只是个管道,但是让管道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是他的责任。从外表来观察,这种生活确实一直有效果——他常被人当做才刚刚50岁——而且这种生活节奏同样是深层愉悦的源泉,这或许也能解释他的作品持续变厚的原因。“这种生活是快乐的生活,所以越多快乐的生活,越多愉悦,书页也就越厚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喜欢读我的长篇作品,但是我现在特别受欢迎。”——这句话不带有一丝傲慢色彩。
他的超高产的工作程序也给他带来了过剩的生产力,于是他就用来写短篇故事,写非虚构作品,还有回答读者的提问,这些问题不只关于他的作品,还有他作为一个心理专栏作家要回答的其他问题。村上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把美国小说翻译成日文:包括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格蕾斯·佩蕾、J·D·塞林格,以及最近的约翰·契弗。
他很享受阅读自己小说的英文译本,因为这就像是读一本全新的小说。“翻译这些大书往往要花费一到两年时间,到了那时候我就什么都忘了,” 他兴奋地模仿着打开书页的动作,“将要发生什么呢?译者会问我:‘你好,春树,你觉得我的翻译如何?’然后我回复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我非常喜欢它!’”
只有当我们的对话转向美国政治时——这场对话也不可避免会谈到这个话题——他才转换语调,表现出更接近于作家的使命感。这个国家的文化对他有深刻影响,当问到他对于美国这场危机的看法时,他在沉默中思考了将近一分钟。然后,他说:“20世纪60年代,当时我是个年轻人,那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我们相信如果努力世界就能变得更好。现在人们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让人很悲哀。人们都说我的书很怪,但在怪异之上,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抵达更好的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先经历怪异。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基本结构:在触及光明之前,你必须先跨过黑暗,穿过地下世界。”
似乎这正是十分契合此刻的一种希望形式。故事结束时,村上的主人公并非必然要学到些什么,他仍然不是圆满幸福的状态,但是他通常会从不平衡的梦境世界转移到一个平和安定的地方。村上的著作似乎在说,生活也许一直很奇怪,但是梦魇终会结束。你会找到丢失的猫。